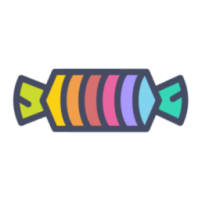听来的故事集(一)
2015年的11月5日晚上11点45分,拉我的司机跟我说了10个字:
你在这里下,我要回去了。
脑筋就比身体慢了1/2秒,我已经下了车,拖着行李走了一路。
天,开始下起了雨。
11年前的那年冬天,曾经也有一个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。11年过去了,这句话,多了后面5个字。而这位作者当时没有留下姓名,以致我每次拿这个段子自嘲的时候,只能双手一摊,很无奈的说道:
我已经忘记那是谁了。
周申健通常第一个拍自己的大腿,
这也太猥琐了!
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,懂得很多。当初对世事不及洞明的我,指的“很多”排除了他用“猥琐”来形容所有他未听闻过的事情这一点。而现在,我真是佩服他。太多我们未曾见闻、未曾经历过的事,到最后用“猥琐”来形容,总比别的更让自己容易接受。
这事情,不能让他知道。
于是我发了一条短信给他,说飞机延误,会很晚才到苏州,今晚就不去打扰,预定了丽晶大宾馆。
他回了我一个字。
丢你……
YES. Delay No More的意思。
在3分钟后,手机电池先丢下我,我拖着行李走了16条街道小巷,大约有一半是重复走过。在尿意憋上头差点从眼里飙出来的一刻之前,我遇见了她。
There’s a crazy little place that I know
Where the drinks are hotter than the chili sauce
And the boss is a cat named Jo.
喂,等等。
你们该不会以为“她”就是这本书的女主吧?
No.
猥琐的我,在街尾遇见了保洁的阿姨,厚起脸皮打听了附近的洗手间。阿姨—你们以为的女主—好心的给我指了巷子里仍在营业的一家店。
“叫Jo的猫”。
这只猫,才是我们的主角。
人喝下的不仅仅是酒,
是一点开心,一点伤感,
是一点回忆,一点心痛,
是一点哀愁,一点郁闷,
还有,
一些无法对别人诉说的故事……
——大家姐
我推开“叫Jo的猫”的店门,把行李箱拖到吧台下面,对着吧台里面抬起头来的姑娘微笑。这个微笑大概持续了3秒,这3秒里我忘词了。
姐哦,请问能借一下洗手间吗?
当我从洗手间出来,姑娘还在收拾刚刚的笑意。
这很尴尬。
我走过去向她致谢。
她问:
你是广东人吗?
嗯?我把五分钟前借洗手间的话在心里念了一遍—并没有卷舌音可暴露—于是好奇的回答,
是。嗯,看得出来?
姑娘又笑了起来,眼角泛起好些笑纹。眼睛下微微浅显的深色处,折出若干岁月痕迹。是位大姑。
你还是潮汕人。
哎呀我的妈!我赶紧把“大姑”这个形容从脑海里删掉,换上“大姑娘”。脸上堆起好多问号。
大姑娘放下擦水的白布,拿起手边的玻璃杯子,倒了一杯温水,推到我面前。
苏州有很多潮汕人。你刚刚说“姐哦”,暴露了。
厉害。
大姑真是厉害。
我心里想。拉过凳子在台边坐下,随手翻开水单看。前面都是一些咖啡、果汁。
要喝点什么吗?
爱尔兰咖啡。
她稍微的迟疑了一下,又笑了起来。
小孩子,看不出你三十好几了。
我大概知道大姑怎么猜到的。这是蔡智恒*《爱尔兰咖啡》书中的情节。痞子蔡的名字,在这本书以后就消匿了。大抵如我这般年龄,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。大姑约莫也是这年纪吧。而一向不爱喝咖啡的我,鬼使神差的脱口而出,可能是记起了“爱尔兰咖啡”的传说:
直到有一天,她决定……,跟他说Farewell,他们的故事才结束。
*蔡智恒,痞子蔡,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作者。
故事结束,值得喝一杯,Caifé Gaelach。
大姑从身后的杯架上,取下一只白身咖啡杯,杯口印着金色的边线,边线下是一只精灵的黑猫,黑猫那圆溜溜的瞳孔仿佛看着我,我朝它努努嘴,嘴里跟它打招呼:
喵。
大姑转过头看我,告诉我它叫Jo。
Hi,Jo.
我也叫Jo。
她平淡的说道。从酒架上扫了一遍,翻出一支褐黄的酒来。酒瓶上写满了我不认识的字,看不懂的画。她转着酒身看了好一会儿,沉默。而后拨开瓶塞,用瓶口贴着咖啡杯的金色边线,缓缓倒下半杯。待到咖啡沫浮出杯面的时候,她拿起旁边的一个金属器皿,往上面随意划了两下,奶沫便荡开了良久的沉默。
我叫So。
她把咖啡放上碟,推到我的面前,侧起头,任一披黑发自然垂下,仿佛在思索着什么。我举起杯子,喝起了这杯传奇咖啡。
这时,空气中传来了一首粤语歌。前面的20秒,我听出来了。
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。
店里很少播粤语歌。
Jo抿着嘴致歉,解释着这首《祝君好》是仅有的了。
我没听见她后面说着什么,刚刚那一口咖啡,混杂着强烈的酒,带着浓郁的咖啡香气和醇厚的酒气,快速流进我的身体,仿佛往最深处的地方冲击,把好不容易埋藏起来的寒冷,或者还有一些雨水,随着漫腾的烈酒,向我的心口狂奔,守不住鼻子酸楚。
好……好冲的咖啡。
她体贴的把餐巾递过来,笑我刚刚没好好听她解释。她没做过所谓的爱尔兰咖啡,所以随性换了底酒,而那底酒是多么的强烈。我没听她说完就喝了一大口,才反应激烈。
原来这样。
我以为喝下的是咖啡,谁知它是酒。
人喝下的不仅仅是酒,
是一点开心,一点伤感,
是一点回忆,一点心痛,
是一点哀愁,一点郁闷,
还有,
一些无法对别人诉说的故事……
甜蜜的时候,苦涩会告诉你,它才是生活的味道;
顺流的时候,逆境会告诉你,它才是生活的路径;
美丽的时候,丑陋会告诉你,它才是生活的真相。
不是我们忘记了,
只是我们贪恋着。
凌晨的脚步,在小巷里踏着雨水徘徊。
喝下半杯那东东—这东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每次都在Jo的茶叶喝完之后出现—我开始觉得恍惚,都忘记早已过了打烊时间。而Jo则在一边静静的坐着,喝着她自己调的酒,听着她自己的歌—据说时不时看看我这个借洗手间的客人,究竟要不要走了。
这样的莫名其妙,在我来到苏州的第一天,遇到第一位朋友。
在后面的日子,周申健时常拿这件事情来猥琐一番,大抵是说我丢下他去丽晶大宾馆,没想到是和Jo。我有时会猜,店里香醇咖啡和酒的味道当中,夹杂异样,会不会是别样意思。
如果他不提,我大概只会记得,那是一个寒冷的雨夜。
十月初五,日历上写着它还在10天以后。而一年后的那一天,我和Jo,和周申健,坐着店里最里面的角落。我又点了这一杯莫名其妙的咖啡或是酒,想着那个远在异国的人。不知道,她是否像我停在这里祝福的她那样,依旧安好。可能,思念才是这杯咖啡的真正味道。
Anyway,
Cast a cold eye,
on life,
on death,
Horseman,
pass by.*
*叶慈诗选。